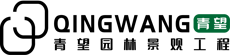在我们的想象中,隐士是非常古老的一类人,比老子孔子更早。比如许由、巢父、善卷等,差不多与尧舜同时。
隐士首先是“士”—一个高贵的人。当君主有道时才可以做官,君主无道时应该辞职,以避免道德上的妥协。所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乘桴浮于海”,归隐去也。在孔子看来避世者是最高的贤者。
这就是中国独特的隐逸山林的文化。既是一种道德的理想方式,也是一种生活的理想方式。但到了魏晋时代,隐逸去处有了微妙的变化,从人迹罕至、未经耕作的、不受人类文明制约的山林荒野,转化为田园了。比如陶渊明笔下的世外桃源,“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这是有人类文明痕迹的自然。陶渊明自己也说:“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吴淇《六朝选诗定论》曾阐发说:“庐之结此,原因南山之佳,太远则喧;若竟在南山深处,又与人境绝。结庐之妙,正在不远不近,可望而见之间,所谓‘在人境’也。”
到了唐朝,隐逸文化的落脚之地又有了改变。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研究,田园生活在唐朝时已悄然转变为园林生活。“这是中国上层社会文化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它标志了一种转变,从中古的‘隐逸’主题转向‘私人天地’(private sphere)的创造。”
唐代园林兴盛带动了都市审美文化需求的高涨。园林本身是城市发展过程的产物与伴生物,是身处都市心存江湖的产物,是用物质条件技术手段对遥远自然的回忆与呼唤,用机械及人工对天然的一种物质模拟。有个西方学者指出:自然风景在西方是市民阶层文化思想的产物,它源于城市的生活方式及由此而形成的对“自然”的渴望。所以,唐代私园主要分布长安、洛阳两京郊区,集于灞、伊、洛诸水之间。而这些私园正是中国庄园的成熟面貌。
什么是庄园?按历史学家韩国磐先生的意见,是封建地主对土地的一种占有形态和经营方式。唐代庄园基本上是自给自足的经济单位,或称庄、庄墅、庄田、别墅、别业等。庄园有大有小,小的只有一顷或不到一顷地,仅有一些住屋和田地;大的则可傍山裹湖,占地百顷。
庄园生活提供了一种非凡的观物方式,宇文所安称其为“私人视角”,这一视角为富有想象力的生活提供了可能。让我们看看一位并不富裕的明代士子李日华在他的小庄园里的闲居生活:李日华是万历年间的进士,后来以养亲为由,退隐至家乡嘉兴。他把家安在水边,门前可以泊船。住所由偃松轩、嘉树堂、美荫斋、味水轩等组成。他的日记记载,他在偃松轩前铺设了五万多块卵石,以免除下雨泥泞之苦。美荫斋因为近旁一棵巨大的古树而得名,坐在美荫斋里听鸟鸣让他极度惬意。嘉树堂得名于堂侧的玉兰树,他每年会在花期移居到这间书房里观赏玉兰。至于味水轩的轩名,一方面是对淡泊生活的隐喻,一方面是他的品茶之地。他对烹茶饮水颇为挑剔,每月一次雇人到二百里外无锡惠山运回“天下第二泉”的泉水数瓮。
那时中国文人的闲居生活,花大量的时间在品茶、饮酒、聚会、闲聊,同时也鉴古、撰文与作画。可以说,庄园文化已经逐渐发展成为一门精致的生活艺术。
其实,无论是中国的庄园,还是俄罗斯的贵族庄园、法国的红酒庄园、英国的乡村庄园,都渊源有自,代表着居住文化的最高形态。
但随着现代社会制度的完善和经济生产效率的飞升,现代版的庄园生活已摒弃了以创收为主的经济属性。日本学者加藤繁认为“庄园,是配置花木、水竹之娱乐游息场所,可除了这部分功能外,大多包有作为生活资料的田地。”从这个定义看,地产商人张宝全在京郊的柿子林与唐代庄园颇为相似,娱乐休息功能得到充分保障,又独立拥有可持续发展和改良的农田果林。但土地的国有性质,让这个“农庄”又不可能像均田制瓦解后的唐宋租佃制庄园。柿子林也无可能出现以庄园为范围、以“族长”为统领的“聚族而居”,时不时过来帮忙做农活的农民或者剪枝、打药、割草、做防火带的工人,更无可能被称为“族众”。
所以,现代庄园的大片用地只能是“租”来的,随时有变更的可能。在离深圳市区50多公里的南澳东山湾海域上,漂浮着商人郭奎章的“海上皇宫”,上有花园、游泳池、跑马场,还有豪华游艇,卧室里都铺着北极熊皮毛总造价大约七八千万元。后被相关部门认定为违法建筑。今年5月,这座存在六年多的奢华海面庄园,最终还是迎来了被拆解的命运。
由于现代庄园的维持成本不菲,而现代的庄园主人也不可能有李日华那样的闲暇时光,庄园的使用率实在不高,当理想主义的情怀渐冷,相当多的私家庄园都在向私人会馆或商业高级会馆转化,有节制地成为企业或个人活动的租用场所。
经济学家认为,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土地将逐渐向少数人手里集中,这是现代农业的必由之路,而这种萌芽或能让中国滋生出第一批真正的庄园主。